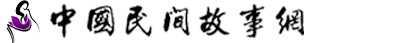来源:网络 作者:佚名
寒假中,我和敏敏、芊芊相约去旅游。在选择旅游地点时,三个人竞会同时说出"普陀山"几个字,真是太巧了,巧得令我们傻眼,令我们兴致勃发。
当我们费尽心机觅到船票时,当我们兴致勃勃踏上旅途时,我们都能从彼此的脸上看到自己的影子,都能找到漾在笑靥中的美好祝愿:青春常驻,友谊长存。
第一次出远门的我们一上船,安置好行囊,便兴奋地跑出船舱,奔至甲板,又从船头跑到船尾,从左舷跑到右舷。
"呜!"起航的笛声响了。
"上海再见啦!""爸爸妈妈再见啦!"仿佛岸边有成群结队的欢送人群,仿佛我们去远航,把那些陌生的旅伴逗得直笑:"嘿……三个小姑娘,疯得来。"
夜幕降临,我们才回到船舱。我们的座位正好是当中的长沙发,和我们隔几相坐的是几位长者。他们见我们坐下,使欣喜地说道:"真是太好了,和三个疯丫头同行一定乐趣无穷,且能激发青春活力。"
我不好意思地说:"我们是第一次外出旅游,难免有些兴奋异常。请各位叔叔、伯伯多多关照。"
于是,我们聊起了关于"第一次……"的话题。机灵的敏敏提议让几位长者每人说段自己第一次的经历。长得慈眉善目的戎林伯伯不由感叹起来:"人的一生中有多少个难忘的第一次,第一次背上书包上学的喜悦,第二次获得成功的激动,初为人父的惊喜,等等。正是这些无数个第一次,构成了我们五彩斑斓的人生?quot;感慨之后,戎林伯伯讲起了少年时代的故事一一
第一次熬鸡汤
都怪我那时太没经验,头一回给妈妈熬鸡汤就熬出个天大的笑话。
那年,我上高一,一直住在学校,平时很少回家。有一次,听说妈妈病了,我便决定回家看看。
动身之前我就在想,给妈妈带点什么回去呢?思来想去,决定买几只老母鸡给妈妈熬汤喝。鸡汤很补,妈妈喝了身体一定会健康的。那时没有现在这么多花样翻新的保健品,惟有鸡汤,算是一种奢侈品了。
我把所有的零用钱加到一起,数了数,觉得够买几只老母鸡了,便跑到离学校不远的乡下买了三只黄黄的老母鸡,用一只装化肥的编织袋把它们统统装起来,捆在车架上,飞一般地往家里骑。
回到家,打开一看,糟糕,两只鸡已奄奄一息,只有一只还有点精神,一双红红的眼睛瞪着我,好像在说:"你真坏!"我在心里说:"坏就坏,怎么办呢?"
有趣的是,袋子里还有一只小鸡蛋,好像刚生下不久,热乎乎的,用手摸摸,那鸡蛋竟是软的,一碰就淌黄水,把袋子弄得一塌糊涂。也不知是哪只鸡生的"孩子"。
躺在里面房间的妈妈听见我的声音,高兴得要从床上坐起。我连忙进屋,按住妈妈,要她躺下,并持着袖子对她说,今天做饭的事我全包了。
我一头钻进厨房,信心十足地开始杀鸡--其实也不用杀,它们早已停止了呼吸,我只不过象征性地用刀在它们的脖子上抹两下,然后再把它们放到开水里烫烫。平时我只知道读书写郑�苌侔锫杪枳黾椅瘢��簧惫�Γ��抑�溃�Σ惶蹋��巧砩系拿�前尾坏舻摹?br> 我忙得一头大汗,才好不容易把鸡毛处理干净。接下来,便是开膛剖肚,也就是说,必须把鸡肚子里的肠子啦、心肺啦、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全部扒掉,才能把鸡放进高压锅里煮。但这时的我,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那就是只顾处理鸡的下面部分,忘了处理上面部分,忘了把鸡脖子下面那个极其重要、极容易让人作呕的部件去掉。
还是高压锅厉害,半个小时,鸡们就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我闻到了从里面散发出来的一股股非常好闻的味道。我觉得差不多了,才把锅盖打开,顿时,一股浓浓的鸡肉香味弥漫了整个空间。
就在这时,一位邻居阿姨带着儿子小宝来看望妈妈。小宝一进门,就用鼻子嗅嗅,说了声:"香死人!"我看见他"咕嗜嘟"一声,咽了口吐沫。我上前一步,连忙说:"锅里熬的是鸡汤,我盛一碗给小宝喝。"说着,就把长长的勺子伸到锅里。
锅里的热气已经散尽,我陡然发现鸡汤上漂浮着两个圆圆的、白生生的东西。奇怪,这是什么呢?我把脑袋想得生疼也想不起来它们到底是什么玩艺儿,是从哪里来的?
我没再多想,把勺子伸进锅底来回搅动几下,我听见一阵"沙沙"声,是沙子、碎石走动的那种声音。
阿姨看我在发楞,把头伸过来,睁大了眼细看,也发现那两个来历不明的异物,问我,这是什么,我把头摇摇,说不知道,她从我手里接过勺子,把那两个东西捞上来,左看右看,突然,她大叫一声:"哎呀,你怎么把鸡嗉子也一锅煮了!"
鸡嗉子!嗨,我怎么忘了鸡嗉子呢?鸡素子是鸡消化食物的皮囊,里面全是米粒和沙子、碎石块,还有我想象不出的东西。皮囊里的米粒、稻谷经过高温一煮,全都膨胀起来,漂浮在鸡汤上面。那只破碎了的鸡嗉子沉人锅底,沙子、碎石也便散落开来……
我感到说不出的后悔。
阿姨说:"这些鸡不能吃了,赶快倒掉。"
我心里却在说:"不,书上讲,煮到100度,汤里是不会有细菌的。"我实在舍不得倒掉,这可是我一个多月的伙食费哟。
我把鸡肉捞出来,装在碗里,捧到妈妈面前,而把那些内容复杂的鸡汤全倒 进了下水道。我担心汤里有没煮死的细菌,它们会损害妈妈身体健康的。
妈妈接过碗,问我鸡汤呢?我苦苦一笑,不知怎样回答,但我从妈妈的表情中悟出了什么,心里隐隐作痛。
这件事已过去好多年了,但我一直记在心里,不敢忘记,以后每次熬鸡汤,杀了鸡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先把鸡嗉子扒掉,我不希望鸡汤上漂浮着两个圆圆的、白生生的、让人作呕的东西,更不想听到沙子、石子在锅底走动的声音。
身材魁梧的王平叔叔浑身充满英武之气,举手投足颇具军人风范。一问,他还真参过军。于是,我们缠着他讲军旅生涯中的第一次站岗。可他连连摆手,说:"不行不行,讲出来太丢人了。"原来是这么回事一一
第一次站岗
15岁那年,我成了"娃娃兵"。在最寒冷的季节里,我被分配到太行山最北端的某部新兵连。来接我们的连长姓田,东北人,一脸大胡子,外加一口?quot;疙瘩"普通话,两眼一瞪,如"张飞"似的,特威猛。
到部队的第三天晚上,天气特冷,气温表上显示零下二十多度。大胡子连长一声集合哨,开始给我们"点名"(后来我才明白,内务条令规定连队每周都要点名,专门讲评和布置工作)。
"同志们,由于部队出发执行任务,营区警戒任务将由我们新兵连那疙瘩担任,今晚九点起,一排开始上岗……"哇,今晚就要站岗,我的脑海立刻跳出雷锋那张手握冲锋枪、威风凛凛在站岗的照片。心里那份激动噢,简直无法形容。
我的岗是在半夜十二点。熄灯号响了,我钻进被窝,望着火墙上映射的炉火,心里不断地念叨着刚布置的的口令--"准备",回令--"打仗"。翻来覆去烙了一小时"烧饼"(部队行话:睡不着)。刚迷糊着,觉得有人在摇我,手电光下是大胡子连长,他轻轻问我:"是王平吗?起来跟我去接岗。""接岗?"我的脑子一片空白。
"对,那疙瘩要轻点起床。"
我一下从迷糊中醒来,站岗、站岗了。我摸着黑急忙穿上衣服,推开门"蹬蹬蹬"跑出去。
连长站在门外。"王平,今晚共六个哨位,我是带班员,你自己去二号哨位接岗,害怕不?"
"报告连长,不怕!"我激动得声音都发颤了。
天特别黑,黑得伸手不见五指。让人不由得想起小焙蛱�档墓砝础6プ帕堇�暮�纾�业��沧驳爻�钇�У亩�派谖幻�ァ?br> "口令!"猛地从黑暗中传来一声吆喝,我被吓了一大跳,头皮一麻,声音都变了调:"是、是我,王平。"
"口令!"对方厉声喝道。
口令是什么?今晚口令?一道闪电划过脑际,我兴奋地大叫一声"准备!",憋了一口气也喝道:"回令!"对方答道:"打仗。"好玩!不过很快头皮一凉,乖乖,要真是打仗,我俩刚才这一应一答,军事秘密还不全泄漏得干干净净!
交班的是班长,他拍拍我,说:"这班岗最难站,来回走走别冻伤了。"说着,他把步枪和子弹带交给我,顺手点了支烟,枪刺泛着一团寒光。
"班长,我不会打枪。"
班长乐了,说:"用不着打枪,枪里没子弹,和平年代嘛,做做样子。"
什么?用空枪站岗?我连忙摸摸子弹带,弹夹带仓果真塞的全是报纸,望望漆黑的原野,心想这要是真有坏人来……一股寒气从脊梁爬上来。
"班长,我……"
"没啥子,两班岗一站,胆子就练野了。"
班长走了。四周黑如锅底,静得令人发憷,我后悔极了,咋没带只手电筒呢!摸着那七斤半重的步枪,心里一阵发虚。我使劲睁眼向左右看看,可什么也看不见。不行,我得侦察一下,记得哪本小说上写过,蹲在地上看影,趴在地上听声。于是,我猫下腰来。
果真,远处黑锄锄的树影凸现出来,虎视耽耽地看着我。这个世界仿佛就我一个人,心里空荡荡的。从未有过的一丝孤独和一丝恐俱慢慢遍布全身。
"战友、战友,亲如兄弟……"唱歌可以壮胆,蹲在地上嘴一张又闭上了,夜半歌声,连自个听着都像夜猫子叫。
怎么屁股直冒凉气?摘下手套从大衣底下摸去,吓了一跳,屁股后裂了个口。原来,起床时光顾着激动,把棉裤穿反了,方便门穿在后面,整个穿成开档裤。这一清醒,还发现脚上袜子没穿,身上立刻冷起来,是苦?是害怕?是委曲?说不清。鼻子一酸,我想起妈妈,泪水无声地滑下来掉在地上。
哭了一会,冻得不行,脚也麻了,屁股也疼了,还是站起来。我端起枪,对着前方的树影就刺起来。一枪一枪又一枪,嘿!这倒是个好办法,既热身又壮胆,尽管我还不懂什么是"防左突刺"、"向前一步刺",可一阵前扑后踢,倒也闹出一阵喘。喘一阵,刺一阵;刺一阵,喘一阵。
突然,我仿佛听见什么。我立刻屏住呼吸,汗毛全竖起来了。可一阵风吹过似乎什么也没有。但我绝对相信我的第六感觉,有情况,准确地讲有人在悄悄向我逼进。
我悄悄地退向墙角,慢慢地蹲下去,趴在地上,果然我听到一丝不易察觉的喘息声紧擦着地面,又依稀看到十几米外一团黑影正向哨位蠕动。
"口令!"我色厉荏在地吼起来。对方突然不动,瞬间我清晰地听到两声"劈啪"--枯枝被踩断的声音。
"快出来!不出来我要开枪了!"我努力压粗嗓音,不让对方听出我的稚嫩和我的恐俱。可对方似乎知道我用的是空枪,并不理会我的存在。伴着两声很重的喘息,小树丛竟动了起来。糟糕,他要采取行动,想摸我的哨?想夺我的枪?此时此刻,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悄然而至。我的心狂跳不已,浑身冰凉,手心全是冷汗。
往日看过的小说、电影,那和敌人搏斗的情节,一幕幕在我的脑海中闪现,竟找不出一个和眼前相似的情节。我在明处敌在暗,先藏起来再说,一滚,滚到墙角的树丛里,慢慢地单腿跪下来,把枪刺指向那蠕动着的黑影。
时间一分一秒地捱过,那黑影一直和我对峙着,寒风中己感觉不到自己的存在,就在我快要晕倒的刹那,突然,那黑影又动起来,顺着墙跟蹭了过来,嘴里还满不在乎地"哼哼"着。
"杀--"我撕心裂肺地大叫一声(带哨的连长多年后还戏谑我,那声音好惨),挟着难以言表的仇恨和恐俱,我一刺刀就向黑影猛捅过去。
"噢……"那黑影拖着惨叫声,夺路狂逃。
不一会,闻声赶来的大胡子连长冲过来,只见我两眼发直,一脸豆大的汗,双手端着滴血的步枪,紧靠在哨位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第二天一早,炊事员来报告连长:"兄弟连队跑了一头大肥猪,昨夜倒毙在西围墙外,肚子上有好大一个血窟窿。"
天哪!
没想到书生气十足的剧团编剧小涛叔叔惟一的一次打架经历,竟然发生在第一次下乡演出中,说起这段经历,小问迨宓靡獾厣斐龃竽粗福��导父?quot;嗬!嗬!"。我们不由得伸长脖子细听--
第一次下乡演出
那是在八十年代初,古装戏刚刚重返舞台。我们剧团送戏下乡,在弋江边的河滩上,搭台演出两天。第一天演《林冲雪夜奔梁山》,第二天演《天仙配》。第一天晚上演出时,河滩上站满了观众,盛况空前。当林冲拖着长矛决定奔梁山时,掌声、喝彩声和着滚滚江水久久回荡在青山峡谷之间……
可第二天演出却风云突变。原来,剧团的大牌花旦--七仙女的扮演者丁萍萍突然病倒了,而且七仙女这个角色没有B角。此时,离演出只剩三个小时了。救场如救火。青年演员梅子受命抢排七仙女的角色,剧团上下悬着一颗心,反正是骡子是马只能拉出去溜了。
入夜,河滩上黑压压地站着千把人。开场锣鼓一响,掌声四起。花容月貌的七仙女上场了,香风带圆场,压住了台。观众直楞楞地张着嘴巴看七仙女呢。我往台下一瞥,不由得舒了一口气,暗想:"一切顺利,万事大吉。"
谁知,台下忽然响起一个苍老的声音:"七仙女不是丁萍萍,简直是挂羊头卖狗肉。"这炸雷似的话语立刻在观众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有的人开始大叫起来:"我们要看丁萍萍演的七仙女。"有的人冲到台前边敲台沿板边叫:"丁萍萍出来。"黑暗中,飞上来一块山芋皮砸在天幕上。梅子哭着奔回后台,仙女们也如鸟兽散。团长见状,抓起话筒冲上台去,对观众说道:"乡亲们,七仙女的扮演者丁萍萍同志生病住院了,实在……"团长的话还没说完,观众的嚷嚷声此起彼伏:
"他骗人,今天早上我还看到她的,别想耍我们?quot;
"我们不管,我们要看丁萍萍的戏。"
"叫丁萍萍出来讲话。"
嗵!一块黑糊糊的东西又砸上台,澎!一个天幕灯被砸爆了。团长毕竟是团长,此刻反倒镇静了,他急忙叫人拉上大幕,不然,几千元的天幕就要报废了。我们全体演职员上台搬道具,搬布景。此时,扔上台的东西中有吃的有用的,甚至还有河滩上的鹅卵石。啪!我的额头上被砸了个正着,血,热辣辣地流下来。演职员们纷纷躲到道具箱后面,以躲开流星似的"炮弹"。这时,满脸鲜血的我忍受不住这份屈辱,发疯似的拉开道具箱,操起两把明晃晃的道具钢刀,大叫一声:"弟兄们,操家伙上!"演员队三十来个精壮的光头武生一齐响应:"拼了!"一窝蜂枪刀剑棍呼啦啦全上台了,武生们沿着台沿一字排开。我一个亮相,挥刀一指:"谁敢上来,老子先劈了他。"这架势居然镇住了台下的观众,台下竟静了下来。有人叫了一声:"戏班子有武功,别上去。"此时,侧幕传出武场急急风的锣声,声震河谷。我也顾不得擦去脸上的鲜血,与乐队一对眼神:"弟兄们,露一手啊!"武生们练开了,虎跳键子后空翻,拉拉提,大甩穗,筋斗一个比一个高,一个比一个飘;单刀进枪,小快枪,双刀棍,开打一个比一个快,一个比一个狠……七仙女们上来了,前桥后桥,原地小翻,云手山膀……文生们也上来了,扇子翻飞,水袖劲舞……台下鸦雀无声。团长见镇住了场,暗自高兴,正准备让我去包扎一下额上的伤口。谁知,台下又传出一个怪叫声:"我们人多不怕他们,冲上去。"先前的宁静被打破了,观众又骡动起来,又有东西扔上台来。我此刻真是气不打一处来,冲到台沿前用刀尖指着那个怪叫者,那个人竟想拉我的脚,被我顺势用力一端,摔了个仰面朝天。台下顿时哄乱起来:"戏班子打人啦!"有的人边叫边冲上台来。一场混战开始了,剧团的演员和工作人员,以及看戏的观众分别扮演了这场武戏的"角色",局面到了难以收拾的地步。我怎么也没想到第一次送戏下乡演出,竟会落得如此结局。
突然,河滩边响起一个清脆的女声:"别打了,我来了。"所有的人立刻如同电影中的"定格"镜头一样僵住了。当他们回过神来,才发现说话者就是当红花旦丁萍萍。只见丁萍萍在团长的搀扶下走上舞台,接过话筒说:"乡亲们,对不起,我在医院打点滴。听说大家点名要我出场,我非常感动,这是大家对我的厚爱和鞭策。所以,我硬撑着来了,请大家稍等一下,我去化化妆。"台下一片寂静,静得能听到天籁……
第二天,丁萍萍的病房里堆满了好多吃的用的东西,还有孩子们送来的彩色鹅卵石。
剧团离开的那天,村里精壮的男子汉帮着挑行头箱;妇女和孩子都来送行;老人们什么话也不说,用眼睛把剧团送得远远的。这里有说不清的理,道不完的情。
刘戎叔叔是旅行社的导游,坐飞机如坐公共汽车似的,可说起第一次坐飞机的经历,令我们开怀大笑一一
第一次乘飞机
七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从没乘过飞机的我听说从阜阳到合肥有飞机可乘,每张票仅要十四块钱,便托人买了一张。乘机前,我特意绕道老家,在那个绿阴如盖的小村庄住了几天,一是等机,二是向那些连汽车也没见过的父老乡亲们吹吹我即将飞上蓝天的心情。那时老乡们太穷,临别时,你送我一袋枣,他送我一瓢豆,村东的王奶奶,竟然送给我十个大鸡蛋。
那原是一架喷洒农药的小飞机,因革命需要而充当了民航班机。我登上飞机时,己有好几位捷足先登了。我数了数,机舱里只能坐八九个人。我对面是一位年轻的妈妈,怀里抱着一个吃奶的娃娃,那娃娃把半个脑袋埋在妈妈怀里,用一只眼打量着这仅有几平方米的机舱,眼里流露出几多惊喜。
我的位子在驾驶台后面,转过脸就能欣赏到驾驶员那神色庄重的面孔和他面前那一排排闪着光亮的各种仪表。我刚把屁股撂到椅子上,就听他在问:"差不多了吧?"坐在他旁边的一位空中大姐说:"差不多了。"于是,他把某个按钮一揿,我只觉得身子猛地向上一提,就那么随着飞机一起升上了高空。
身边是一只小面盆大小的窗户,从窗户朝下看,能看见一条条马路,一片片田畴。田里有人在浇水,有人在翻地。几辆驴车在大路上狂奔。开始,田野像一个硕大的棋盘,渐渐地变成巴掌大小,人也变得像蚂蚁一样。我的心底升起了莫名的悲凉,原来不知天高地厚的我竟是如此渺小。
我的视野里出现了一条白色的银链,我断定那便是淮河了。进人丘陵地带之后,机身开始抖动,越往上抖得越猛。我的心也在胸膛里跳个不停。转过头一看,驾驶员好像也乱了阵脚,一会捣捣这里,一会揿揿那里,可飞机还在抖个不停。我发现他的脸色由红变白,由白又变青。一种不祥的预感迅速占据了我的整个心灵。就在这时,那位空中大姐走到大家面前,将两只胳膊抬起,做了个向下按的动作,我听不清她在说什么,意思大概是不要慌,就会好的。
我实在不明白她所说的"好"是什么意思,难道飞机出了故障?我再也不能平静,思绪被嗡嗡的机器声搅得粉碎。从历史上无数飞机失事想到我那刚上小学的儿子,想到抱病在床的妻子,想到倚门盼我归来的母亲--我想我是不是应该写封遗书什么的,可空中大姐一直没有交待,我不好意思在众目睽睽下掏出纸笔。
"咕冬"一声,什么东西倒了,我以为是飞机的门被风吹开,用眼角一瞟,才知道是我那该死的背包瘫痪在地。
空中大姐转了几圈,终于回到原来的位子。
不知又过了多久,飞机慢慢地下降,窗外出现了一片碧绿的草地。飞机再往下降时,我看见那半人深的荒草在巨大气流的冲击下发疯似的向一边倾倒。我还看见高高的了望塔,看见在机场上打旗子的领航员,看见了一切离死神很远很远的生命。
飞机停了,舱门大开,我逃也似的跳了出来。是空中大姐叫住了我,把那只包递到我的手上,我这才想起我的背包。她说些什么,我一句也听不清。我怀疑是飞机的轰鸣声把我的耳膜震破了。大姐指指旁边的一排小平房,让我进去歇歇。
我在这个挂着候机室牌子的建筑物里足足坐了一个小时零八分,听力才渐渐恢复。捏捏背包,所有的豆类枣类安然无恙,鸡蛋却不异而飞,伸手摸摸,湿漉漉的,打开一看,天哪,这些小狗日的,胆子比我还小,全吓得稀烂。
听罢他们的"第一次故事",我想:我们的第一次旅游又会发生什么样的故事呢?是平平安安。波澜不惊?还是……不过,与他们的相遇,不也是我们第一次旅游中一段令人难忘的序曲吗?
转载请注明转载网址:
http://www.gushigu.cn/news/xiandaigs/073272016576AIF9K8G1B4KHDJ625FH.htm
【相关内容】
|
佚名 |
|
佚名 |
|
东 风 |